
光合作用示意图。图片来源:wikipedia
2009年的一个早晨,我乘着一辆吱吱作响的大巴沿着哥斯达黎加中部的山坡蜿蜒前行。我攥着许多行李箱,被柴油烟雾熏得头晕目眩。箱子里有上千只试管和样品瓶、一把牙刷、一本防水笔记本和两套换洗的衣服。
我正在前往拉塞尔瓦生物研究站的路上。在那里,我将花几个月时间研究潮湿的低地雨林在日益干旱的气候下会发生的变化。狭窄的公路两旁,树木像在水彩画中一样与薄雾交融,仿佛云雾缭绕的、无垠的原始森林。
我凝视着窗外壮观的景色,不禁感叹我怎么会奢望理解如此复杂的景观。我知道,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都在致力于研究这一课题,尝试理解热带森林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的命运。
我们人类社会对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要求太高了,它们承担着数百万人的淡水供应,也是地球上三分之二陆生生物的家园。近来,我们还对这些森林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它们救我们于人类自身造成的气候变化的恶果。
植物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将其转变为树叶、木头和根系。这个每天都在发生的奇迹让人们产生了一些希望,即用植物——特别是快速生长的热带树木——作为气候变化的天然制动器,捕获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大部分二氧化碳。世界各地的政府、公司和慈善保护机构都承诺保护或种植大量的树木。
但事实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树木来抵消社会的碳排放,而且永远都不会有。近来,我回顾现有的科学文献,以评估森林可以吸收的碳量。如果我们将目前地球上的植被量最大化,吸收足够多的碳,能抵消目前排放速度下约十年的温室气体。但在那之后,就无法再进一步的捕获更多的碳了。
然而,我们人类的命运和森林以及它包含的生物多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急于种植数百万棵树木来捕获碳,这会不会反而破坏了它们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森林属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植物如何吸收二氧化碳,还要考虑它们如何为陆地生态系统提供坚实的绿色基础。
植物如何对抗气候变化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单糖。这些糖类随后被用来构建植物的生命体。如果被捕获的碳最终进入木材,它就可以离开大气,被锁住数十年。当植物死亡时,它们的组织会腐烂并被吸收到土壤中。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会分解死亡的生物体,并通过呼吸作用释放出二氧化碳,但部分植物碳还是可以在地下保留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总的来说,陆地上的植物和土壤能够容纳约2500亿吨的碳——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4倍。
因为植物(尤其是树木)是如此理想的天然碳储存库,所以通过增加世界各地的植物数量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有道理的。
植物生长需要四个基本要素:光照、二氧化碳、水和营养物质(如氮和磷,与植物肥料中的元素相同)。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在研究植物生长与这四种成分的关系,以预测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人类同时改变了自然环境的许多方面,例如让全球变暖,改变了降雨模式,砍伐了大片森林,以及将外地物种引入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陆地上还有超过35万种开花植物,每一种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应对环境的挑战。
由于人类改变地球的方式十分复杂,科学界对植物能够从大气中吸收的确切碳量也存在很多争议。但研究人员一致认为,陆地生态系统吸收碳的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给树木提供充足的水分,森林就会长得又高又茂盛,长出成荫的树冠,使周围更小的树失去光照。如果我们增加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植物会急切地吸收它——直到它们再也无法从土壤中吸取足够的肥料来满足它们的需求。就像面点师制作蛋糕一样,植物需要特定比例的二氧化碳、氮和磷,有着特定的“食谱”。

茂盛的森林会让更矮小的植物失去光照。图片来源:Pixabay
考虑到这些基本限制,科学家们估计,地球陆地生态系统还可以额外容纳的植被能吸收大气中400至1000亿吨碳。而一旦实现了这一额外的增长(这一过程将要花费数十年),陆地就无法再提供更多的碳储存了。
但是,我们的社会正以每年100亿吨碳的速度将二氧化碳排入大气。自然过程很难跟上全球排放温室气体的步伐。例如,我曾计算过,从墨尔本到纽约市的往返飞行中,一名乘客所排放的碳(1600公斤碳)大约是一棵直径半米的橡树所含碳(750公斤)的两倍。
危险与希望
尽管植物生长存在这些物理限制,人们仍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努力来增加植被的覆盖率,以缓解气候紧急情况——即所谓的“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因为树木的生物量比灌木或草要多很多倍,它们有更大的碳捕获潜力,所以绝大多数努力都集中在保护或增加森林。
然而,从根本上误解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捕获能力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种植树木怎么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呢?
答案就在于自然生态系统在碳捕获上微妙的复杂性。为了避免对环境的破坏,我们必须避免在自然界中本不应有森林的地方种植森林,避免为种植新的树木而砍伐现有的森林,并且审慎考虑今天种植的树苗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进行任何森林的扩展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树木被种植在正确的地方,因为并非所有陆地上的生态系统都能够或应该支持树木的生长。在本应种植其他类型的植被的生态系统中种植另外的树木,往往无法实现长期的碳封存。
一个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来自苏格兰泥炭地——在那里,大片的低洼植被(主要是苔藓和草)生长在常年湿润的土地上。在酸性且浸满水的土壤中,死亡植物的分解非常缓慢,因而逐渐积累起来,长此以往形成泥炭。被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植被:泥炭沼泽中还保存着所谓的“沼泽尸体”——千年前死去的男女的几乎完整的遗体在其中形成了“木乃伊”。事实上,英国泥炭地的碳含量是全英国森林中的20倍。

泥炭地。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是,在20世纪末,苏格兰的一些沼泽地被抽干用于植树。干燥的土壤令树苗难以生长,这种改变还导致泥炭的腐烂速度加快。生态学家Nina Friggens和她在埃克塞特大学的同事估计,干燥泥炭的分解所释放的碳比生长中的树木所能吸收的碳还要多。显然,就泥炭地而言,任其自然发展反而能最好地保护环境。
草原及稀树草原的情况也是如此。火是这类环境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本不该种植在那里的树木经常被烧毁。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北极苔原,那里的原生植被在整个冬季都被冰雪覆盖,并反射光和热。在这些地区种植高大的深色叶子的树木会增加对热能的吸收,从而导致当地变暖。
即使在林地种植树木也可能导致负面的环境结果。从碳封存和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森林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自然形成的森林比人工林包含更多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它们通常也会容纳更多的碳。但是,旨在促进植树造林的政策可能无意中激励了那些对现有自然森林砍伐的行为。
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是墨西哥政府的“Sembrando Vida”(播种生命)计划,该计划会为土地所有者的植树betway官网提供直接支持。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许多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会砍掉成熟的老树林来种植树苗。这个决定,虽然从经济角度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却导致了数万公顷成熟森林被毁。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狭隘地将树木看作碳吸收机器可能存在的风险。许多组织出于好意去寻求生长最快的树木,因为这在理论上意味着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速度更快。
然而,从气候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一棵树能生长多快,而是它在成熟时含有多少碳,以及这些碳在生态系统中能停留多长时间。森林在老化中达到了生态学家所说的“稳定状态”,这时树木每年吸收的碳量与植物本身和地下数万亿微生物呼吸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完全平衡。
但是,这一现象还会导致另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成熟的森林对于气候减缓没有用处,因为它们不再快速生长和吸收额外的二氧化碳。与这一看法对应的错误“解决方案”是将植树的优先级放在保护现有森林之前。这就好比把浴缸里的水放掉,以便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龙头的水流比以前大了,但浴缸的总容量并没有改变。成熟的森林就像充满碳的浴缸,它们对容纳陆地上大量而有限的碳有着重要贡献,扰乱它们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如果每隔几十年就砍伐一次森林来重新种植,并将砍下的木材用于其他保护气候的目的,会怎样?其实,若砍伐的木材最终用于长期使用的物品(如房屋或其他建筑),这可以成为非常好的碳储存方式,但事实上,只有极少的木材以这种方式被使用。
同样,将木材作为生物燃料燃烧,减少化石燃料的总消耗,可能会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生物燃料种植园几乎没有对管理的森林提供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一些研究从一开始就在质疑生物燃料本身对气候的好处。
为整片森林施肥
如何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捕获量进行估计取决于这些系统将如何应对未来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挑战。地球上所有的森林——即使是最原始的森林——都容易受到气候变暖、降雨量变化、日益严重的野火和通过地球大气流漂移的污染物的影响。
然而,其中一些污染物含有大量的氮(植物肥料),有可能给全球森林的增长提供养料。通过生产大量的农业化学品和使用化石燃料,人类已经大大增加了可供植物使用的“活性”氮。一些氮能溶解在雨水中到达森林地表,在某些地区可以刺激树木生长。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年轻研究员,我很好奇一种未被充分研究的生态系统——季节性干旱热带森林——是否会对这种效应有特别的反应。我发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出答案:给整片森林施肥。
我与我的博士后导师,生态学家Jennifer Powers和植物学家Daniel Pérez Avilez合作,选定一片约两个足球场大的森林区域,并将其分为16块,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肥料处理组中。在接下来的3年里(2015年-2017年),这些块地成为地球上被研究最深入的森林区域之一。我们用专业的、手工制作的植物生长测量仪来测量每棵树树干的生长。

用测量仪测量树干的生长。图片来源:原文
我们用篮子接住树上掉下来的枯叶,并在地面上安装了网袋来追踪根部的生长情况。在我们费力地洗净这些根部的土壤后将其称重。实验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施肥本身,每年需进行三次。我们穿着雨衣,戴着护目镜来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受腐蚀性化学品的伤害;拖着背负式喷雾器进入密林,确保化学品被均匀地喷洒在林地上,而我们在橡胶大衣下汗流浃背。
不幸的是,我们的装备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愤怒黄蜂的攻击,它们的巢穴往往隐藏在悬空的树枝上。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3年后,我们可以计算出每块土地上产生的所有树叶、木材和树根的质量,并评估了在研究期间捕获的碳量。我们发现,森林中的大多数树木并没有从肥料中受益——与之相反,它们的生长与特定年份的降雨量密切相关。
这表明,如果干旱继续加剧,气体中氮元素也不会促进这些森林中的树木生长。为了对其他森林类型(更湿或更干等)做出同样的预测,我们需要重复这样的研究,以扩充几十年来通过类似的实验积累下的知识库。然而,研究人员是在与时间赛跑。这样的实验是缓慢、辛苦而繁重的,而人类改变地球面貌的速度超过了科学界能做出反应的速度。
人类需要健康的森林
支持自然生态系统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一件重要武器。但是,陆地生态系统将永远无法吸收化石燃料燃烧所释放的碳量。我们不应再被植树计划蒙蔽,而需要从源头上切断排放,并寻找其他的战略来消除已在大气中积累的碳。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保护和扩大森林的举措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当然不是。保护和扩大自然栖息地,尤其是森林,对于保证地球的健康绝对是重要的。温带和热带地区的森林中生活着五分之四的陆地物种,但它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我们星球上近一半的宜居土地被用于农业,为了耕地或牧场而砍伐森林的行为还在不断发生。
同时,气候变化造成的大气混乱正在加剧野火和干旱情况,并使地球升温,这对森林和在其中生活的野生动物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即自然界能为人类提供的众多好处)之间的紧密联系。

干旱的土地。图片来源:Pixabay
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生物能提供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药物活性化合物,激发了新药的产生。它们还直接(想想数百万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是野生鱼)和间接(例如很大一部分农作物归功于野生动物授粉)地保证了人类的粮食安全。
自然生态系统和其中数以百万计的物种还在不断激励着技术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变化。以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为例,它能帮助警察抓住罪犯,也使得你所在地区的药房能够提供COVID测试。聚合酶链式反应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一种生活在温泉的不起眼的细菌所合成的一种特殊蛋白质。
作为一名生态学家,我很担心现在人们过分简单化森林在缓解气候危机中的作用会无意中导致森林的衰退。许多在植树方面的工作都集中在种植树苗或其增加植物的初始生长速度上,但这两者都不能很好地反映森林最终的碳储存能力,更不能反映生物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将自然生态系统视为“气候解决方案”会给人带来误导,人们会误认为森林可以像一个无限吸收的拖把一样不断清理人为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
幸运的是,也有许多致力于森林扩张的大型组织正在将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纳入其成功的衡量标准。一年多以前,我参观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一个巨大的重新造林实验,该实验由世界上最大的植树组织之一“Plant-for-the-Planet”运作。意识到在恢复大规模生态系统中所固有的挑战后,该组织发起了一系列实验,以理解在森林发展早期,不同的干预措施将如何提高树木的存活率。
这还不是全部。在科学主任Leland Werden的领导下,该基地的研究人员将研究在森林生长的过程中如何为种子提供理想的环境使其发芽和生长,以助力当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这些实验还将帮助土地管理者决定何时何地植树对生态系统有利,以及何处的森林再生可以自然发生。
我明白将森林视为生物多样性的储藏库,而不是简单的碳储存库,会使决策复杂化,并可能需要政策的转变,我非常清楚这将带来的挑战。我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在研究和思考碳循环问题,而我自己也常常见木不见林。几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坐在哥斯达黎加的雨林地面上,测量土壤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一个相对耗时和孤独的过程。
在我等待测量结束时,我发现一只草莓箭毒蛙——一种微小的、有宝石光泽的动物,只有我的拇指大小——在附近的树干上跳跃。我好奇地看着它走向一个带刺植物叶子里的小水潭,里面有几只小蝌蚪在游动。青蛙到达这个微型水族馆后,那些小蝌蚪(是她的孩子)就会兴奋地振动,而它们的母亲则把未受精的卵放在那里让它们吃。后来我知道,这个物种的青蛙(Oophaga pumilio)非常勤奋地照顾它们的后代,母亲每天都要重复的长途旅行,直到小蝌蚪发育成青蛙。

草莓箭毒蛙。图片来源:wikipedia
当我收拾好设备准备返回实验室时,我突然想到,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小剧目正在我身边上演。森林不仅仅是碳储存,它们是不可知的复杂的绿色网络,将数以百万计的已知物种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待发现物种。为了在全球剧烈变化的未来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紧密缠绕的网络,也尊重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撰文:Bonnie Waring,伦敦帝国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气候变化与环境高级讲师。
翻译:刘思洁
审校:费哲妮
引进来源:theconversation

本文来自:betway官网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科普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其它相关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责任编辑:环球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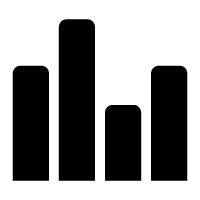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9775号





